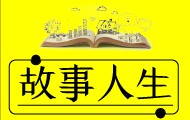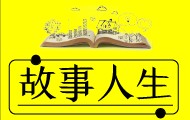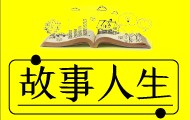【智慧】就业路上
【阅读提示】
李超的故事在很多常人的眼中平淡而普通,他没有优越的家庭、良好的教育、出色的成绩,在残障人谋求生存可能的各种手段和方式中,李超放弃了等待和依赖,寻求就业和独立,因而面对就业背后所承载的诸多东西,收入、婚姻、社会地位、个人价值、社会保障等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有工作是第一目标
李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说话痛快、京味十足、声音粗矿、长相老成,如果不是他告诉我们,很难猜到他的年龄只有26岁。
李超有智力障碍,但在表达和沟通方面还比较顺畅,他告诉我们,他是由舅舅和姥爷抚养长大的,爸爸因为在文革期间由于大字报和批斗的原因受到惊吓,精神不好需要长期住院,他自己并没有见过,只是听说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姥姥把父亲从医院接出来,抱了一下儿子又送回医院去了。李超的母亲又因为吃药不当,精神也不太好,照顾自己都有些困难,所以,出生后的6个月开始,李超就一直跟着他的舅舅。
就这样一直顺利地上到了小学六年级,由于李超的成绩一直很差,没有跟上学校的进度,学校最终出于对升学率的考量,通知了他的舅舅,要求李超去查智商,北医三院最终确认李超的智商在60-70之间,于是,他被转到了培智学校。
在我们看来,在没有任何辅助的情况下,能够在普通学校上到六年级,李超的障碍应该是轻度的了,那么,像他这样的情况进入培智学校,在学习上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但是,李超说:“在培智学校其实就是换个环境,进那个学校的智商都不是很低,一般培智学校收的智障人士智商也不是太低,收轻度点的,六七十、七八十左右的,太重的不要,学校会教基本的识字,能看报纸就行,这还是其次,主要学一些手艺”。
为了说明培智学校只招收轻度智障的情况,李超还给我们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培智学校的学生是需要穿校服的,校服上面也印着培智学校,但是,只要出了学校,他们都不会穿,而且在回家的路上就脱掉了。
到了16岁,李超从培智学校毕业了,说是毕业,实际上培智学校是按年龄毕业的,只要到了16岁,学校就不再负责了,也是到了应该工作的时候了。一般而言,从培智学校毕业后的智障人士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当然,家庭所在的街道也需要做一些工作。
李超说,他们街道办事处因为需要找工作的人太多,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帮助他找到工作,唯一有过一次面试机会,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了。
就这样在家呆了一年多,最终在舅舅的帮忙下,李超找到了一家离家不远的小饭馆,做起了学徒,主要是跟着临时工学杂活。
“从杂工,刷碗、择菜、杀鱼,切蒜末、切姜末、切个辣椒末开始学起的,因为饭馆基本就是这些东西吧”李超回忆起来如数家珍,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累,“刚开始挺累的,干了一天腰就起不来了,因为没干过这么多的量,受不了。”
因为是小饭馆,也因为是学徒,所以,工资肯定不会太高,只有800-900之间,李超并没有因为太累、工资太低而选择回家待着,“父母身体都不好,还得靠自己,而且我在家还领不到低保”。李超的父亲和母亲双方的单位有比较好的保障,但只够他们自己的日常花费。
说到现有的低保以家庭收入为标准,李超的看法显得有些矛盾,似乎在他心里对此有些不满而又有些理解,更多的是觉得这个和自己关系不大,自己不会与低保为伍的,李超说:“不合理,工资高跟我也没关系啊。但是这东西也是很公平的,老靠着国家你自己也没什么上进心了。好多像我们这样的残疾人能上班的不上班,非得吃低保,那有什么用啊?中国这么多残疾人没工作都吃低保,不可能大家都能吃上。”
从小饭馆离开的时候,李超这个学徒还真是学了一身的本领。“杀鱼就是把鱼拍死之后,刮鳞、抠腮、开膛,完了之后拿水里一涮,还有草鱼的苦胆不能弄破了,弄破了得赶快去洗。还杀过牛蛙,把脑袋剁了,把皮一扒,还有鸡、鸭呢,鸡老板买的都是死的,就给开膛,把里面的鸡胗、鸡心留着,还能做别的东西”
回炉再提高
2005年,丰台区的一家民间公益机构利智中心通过街道的推荐找到了李超,因为是民间机构,所以主要就是针对公立培智学校的空白,比如为重度智障提供托养服务,而李超这样超过培智学校年龄的,在那里可以继续学习,听说可以学习,也有人“教怎么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李超欣然前往。
2006年,利智的插花项目启动了,李超也成了第一批的学员“他们问我你想不想上班,我说想上班。”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初级、中级考试,李超对插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不就修个花嘛,往里一插就完了,就是花形嘛,扇形之类的,其实不用配色,你可以选易用色的康乃馨去插”
李超还认为自己是学的最好最快的一个。“学生里面我是学最快的,因为我是不会就问,不会就问,给人问烦了我也学会了。2006年有10个人,学完了之后那10 个人就没有几个了,一起考中级的时候就只有5个。”
在利智的努力下,插花的项目在学习、考试以及销售层面同时展开,但尽管如此,与小饭馆的杂工相比,李超的收入也没能有明显的提高,但他却认为,小饭馆里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在这可以学的更多,以后可以立足。
为了扩大插花项目的成果,2010年利智中心在世界公园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并聘请了一个插花师带着李超和几个智障学生开始了支持性就业的实践,从学校的插花车间走到了社会上。所谓支持性就业,就是相对于原来封闭的就业形态,指在类似花店这样的主流环境中,通过一定的支持使智障人士和大家一起工作,同工同酬。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花店未能持续,2011年4月,北京利智又和万丰小吃城签订了摊位租借的合同,根据经营的状况,每年签一次,租了两个位置相近的摊位,继续进行支持性就业的实践,一个摊位卖凉菜,一个摊位卖砂锅,卖凉菜的师傅是外请的,并且带着智障学生做砂锅,

李超每天的工作准备
李超也就顺利转到了现在的岗位:砂锅师傅,“沙锅也算是一种手艺,但和厨师不同,厨师炒东西挺麻烦的,炒生了也不行炒老了也不行。沙锅好掌握,炒菜不一样,掌握不好就老了,别人咬不动,太生没熟也不行,砂锅要求没这么高,我学得了。”
李超由师傅带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开始独立工作了“炖牛肉、卖牛腩,还得炸丸子,都得会不难,弄沙锅的汤料也简单,就是搁点鸡架子,搁点棒子骨就行了,白肉就是白水煮,都不难,主要就是切白肉的刀工比较难。”
说道“切白肉”,李超觉得这是目前他最大的挑战“切得肉不够薄,就是要跟纸那么薄,肉不能冻太硬了,这的冰箱都是冷藏箱,稍微冻一下就切,切得越薄越好。……薄的不是显多,切得厚几块就满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切肉的原因,李超还遇到过被懂行的顾客点名要求换一个师傅做。
工作的烦恼
每天的工作,李超10点要到万丰小吃城,开始准备东西,装上砂锅,然后摆上,中午两点才能吃饭,然后下午是四点半上班,晚上九点下班。这一天也够8小时,一周要上六天的班,只有周五一天的休息时间,中午饭就地解决,“炒白菜,在下点肉,闷米饭,有时候吃点馅饼。”客人少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间也会和其他师傅打牌。
因为做砂锅的时间长了,李超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察:“王府井全是卖服装的,人家买完衣服去吃饭,做生意就忌讳没有卖服装的,生意没有来源。……附近小区的人不在这吃,一般上网看才到这吃,还有一些旅游团,这里的人不到这吃,不好吃,太贵,充100块钱,还有10块钱押金,90块钱一会儿就没了。”
对于目前的工作,李超为自己的将来有些担忧,怕长不了,得走人。“我希望在一个地方一干50年干到退休为止,工资不太高,工资给我1800就行,给我上保险就行。”
比起工作,他目前更大的心愿就是找一个女朋友“我好多同学都结婚了有孩子了,还有一个同学她有一个闺女,她老公也是我们学校的。……找一个能过日子的,会管家的,把一块钱掰两半花的是最好的,那种人该花的她花,不该花的不会瞎花的。”

▲ 李超在摊位前
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李超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告别,来了一句大吆喝,这也是他每天工作的重要内容“砂锅居的砂锅,砂锅丸子、砂锅白肉,有荤的有素的,还有馅饼、葱花饼,现吃现烙……砂锅居的砂锅,牛腩、白肉、豆腐、鱼丸,有荤有素。”
【人物介绍】
李超:男,智力障碍,1994年就读西罗园三小,1999年转入方庄培智学校学习,2002年毕业,2003年在小饭馆从事学徒和杂工工作,2005年进入丰台利智中心学习,2006-2007年间分别考取插花师初级和中级证书,并在利智插花车间工作,2010年在利智所开设的花店工作,2011年起在万丰小吃城先后学习和承担砂锅制作工作。
【编者随想】
在以数字为标准的考核体系下,人们往往选择较易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在智障人士的教育和就业方面,公立的培智学校一般招收轻度智障的,基层的就业服务一般针对轻度智障的,因为,更容易实现“数据”,那么,中重度的智障人士呢?他们即使在智障群体里也要面对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
在李超的摊位后面,有一块智障人支持性就业的牌匾,但并没有放在显眼的位置,据李超的介绍,刚开始没有生意的时候,会把那个牌子放在比较明显的位置,后来,生意渐渐好转后,发现这块牌子反而会影响一些顾客的看法,对他做的食物产生顾虑。所以,残障和非残障在同情和怜悯基础上其实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

▲ 支持性就业的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