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眼】郑璇:我是谁
【阅读提示】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刻或因为某种原因处于主流之外、被边缘化的境地. 而这种情况,在聋人群体体现的尤为显著。强烈的融入主流愿望,使他们按照主流的方式说话、表达,并以主流的标准衡量自己,失去了对于自我身份和文化的认同,进入了另类边缘化和自卑的死循环。郑璇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融入并非一味的跟随和趋同,而是在自信和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碰撞产生的交流、融合与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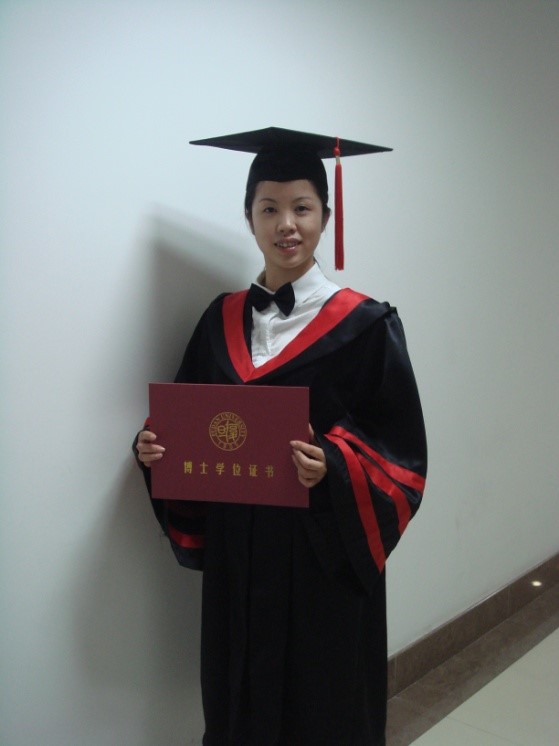
▲ 博士学位照
家庭早教:发音并不代表语言
郑璇出生在武汉。天生活泼、聪明的她,是全家欢乐的源泉,1983年秋,刚满两岁的郑璇,在治疗感冒的过程中被注射了过量的卡那霉素导致耳聋。卡那霉素是一种“耳毒性药物”,使用过量会引起听力减退甚至消失。医院的诊断结果令人绝望,郑璇患极重度神经性耳聋,属于“听力一级残疾”。
“我的听力损失程度,左耳是95分贝,右耳是110分贝,在不带助听设备的情况下,音量比95分贝大的声音我才能听得见。我们平时听到的正常交谈的音量大概是四五十分贝左右,高声喊叫的音量是在70到80左右,高音喇叭的声音大概是在90分贝左右。”按照这样的情况,郑璇基本属于全聋了。
而神经性耳聋更是被看作医学上的绝症,一家人多方求医,求得的都是同样令人绝望的结论。俗话说“十聋九哑”,没有了听觉上的刺激,郑璇很快就把原来所学不多的语言全部忘记,终日沉默,不愿开口。“耳朵坏了,但绝对不能让孩子成为哑巴!”这是父母当时心里唯一的念头。一家人节衣缩食给她买了当时最好的助听器,郑璇感慨的说,假如没有家人一如既往的帮助和努力,不会有今天的郑璇。“他们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没有专业的理论背景,但是,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必须让我能听得到,只有听得到才能有听说正常化的言语链,所以他们不但为我佩戴一些助听设备,而且会一直在我的耳朵边喊。”

▲ 全家福
为了帮助郑璇培养说话的能力,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了武汉,外婆也提前退休来到郑璇身边,康复训练就这样开始了。每天至少有四五个小时,母亲和外婆两个人轮流在她耳边“喊话”,直到两个人嗓子都喊哑了为止。
由于当时的助听器效果较差,加上郑璇发音器官长期不用功能已经退化,即使是常人很容易分辨的语音,在郑璇听来都是模糊不清的。家人从拼音开始教郑璇,韵母a、o、e还算比较顺利,声母z、c、s和j、q、x就困难了,一个字母经常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学。
“语言康复训练本身很枯燥,而且我的听力损失是比较重的,所以他们要贴在我的耳朵喊,我特别不喜欢那个方式,他们在我耳朵边儿喊话气流很大,而且很不舒服。”郑璇一边回忆一边说。
后来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儿歌和故事,每天都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为了不干扰邻居,即使在夏天家里也不得不挂上最厚的窗帘,夏天的武汉堪比火炉,每天全家人就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火炉中,汗如雨下地帮助郑璇练习发音。这种家庭语言康复训练一直进行到五六岁,郑璇逐渐什么话都能说了,虽然发音还很含糊,但聋人开口说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可喜的突破!
聋教育界认为聋人的主要障碍是语言交流障碍,听力和语言相比,语言交流的障碍更大一些,但是当很多孩子失聪之后,家长把注意力放在治疗耳朵上,或者花很多的时间教他们说一些简单的字词,进行一些机械的“语音”康复而不是语言康复。比如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康复中心去,呆了半年学会说“爸爸、妈妈”,却忽略了整个语言的掌握,失去了发展汉语能力的黄金时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郑璇的父母显然没有这样做,他们对郑璇有着更高的期望和信任。

▲ 十岁生日
学生时代:适应主流就是不搞特殊?
郑璇走进了普通小学的校门。当时她不会手语,郑璇的父母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她送到聋校上学,而是一如既往不厌其烦的认真教导她像普通孩子一样学习。他们特别注重郑璇的汉语写作训练,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她写作文,这些写作训练为郑璇的文字表达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郑璇在小学的时候并不顺利。由于与人交流不便,她在同学中不受欢迎,经常成为同学们恶作剧的对象,助听器被抢走丢进水沟,进教室时被门框上的扫把砸到,被淘气的女生扇耳光,这样的遭遇屡屡发生,虽然那时的郑璇也会生气、抱怨,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上学。
“有一次全班同学拉出来在外面,老师教我们唱歌,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我根据我的理解,感觉他们在唱‘抱我’,我很奇怪,回家问我爸爸,他说那是国歌,是‘炮火’。”说到唱歌,郑璇回忆说:“我记得老师在教唱歌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在唱,我感觉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在里面滥竽充数,我假装我在唱,就特别不高兴。”
从一年级开始郑璇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去适应主流环境,但她感觉到这种适应似乎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每一次下课,因为害怕听不到上课铃,她的选择就是不出去,一直在课桌那里坐着。
“当时没有任何意识说我是一个特殊的孩子,所以我应该理所当然的有一些特殊的措施和特殊的待遇,现在知道那个不是特殊化,而是针对我的特点来给予适合的教育,我当时不知道,我是片面的适应它。”
郑璇的父母也觉得她一定要和普通的孩子一样,他们尽量不给她特殊化,除非是碰到一些学习上的困难:“老师讲课我听不清楚的话,他们非帮助我不可,帮助我预习、帮助我复习,我爸爸每天都帮我批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郑璇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各种学科竞赛中也多次获奖。小学、初中、大学,她在孤独中一路奋力前行,199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
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聋人的选择。然而,言语通道受到了阻碍,反而造就了郑璇文思的活跃。从小就喜欢看书和写文章的她,曾经在各种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就看完了《西游记》的原著,五年级的时候看完了《红楼梦》。“我看的书很杂。”郑璇笑着告诉我们:“自己在家里看爸爸的书,《红岩》、《铁道游击队》、《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各种史书、医书。”她从小特别喜欢唐诗、宋词,小学时就会背诵《长恨歌》、《葬花词》等长诗。她独特的网名“其叶青青”,就是从诗经中得到的灵感。

▲ 教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跳舞
在大学里,模糊晦涩的语言已经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自己买来了普通话培训课本和磁带,自己对自己进行语言康复练习。一次次的朗读、演讲、正音练习,终于,她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克服了方言口音对她的影响。
英语听力是郑璇当时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但她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在100分的满分里有20分的听力,我全部写的C,我想全部写C可以拿4分左右”于是在听力部分完全靠猜测的情况下,分别以78分和61分的成绩拿到了四、六级的证书,四年之后,她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武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学业的顺利反而让郑璇茫然:“我当时面临一个特别严重的身份冲突问题,我当时不想当所谓的听人,我觉得我是聋人,我希望去寻找我的群体。”
郑璇在武汉大学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半走读的状态,和班上同学的互动不多,在健听人中生活感觉让她感到孤独,虽然表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但是交流还是很累,而且一些地方缺乏共同的话题,于是,她在网上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讨厌说话,我觉得很累,因此我学习了手语。学习手语的过程很漫长,因为手语是一个语言,有它的语法和词汇,学习语言不可能很快,不可能在半年、一年内掌握得很好,我学习手语和他们交往也是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才逐渐的和他们真正的相融的,特别是我们手语族的思维和文化跟普通人确实不太一样,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有我们的特点。”
手语分为自然手语和手势汉语两种,郑璇告诉我们,它们的语法并不一样。如果是出生在聋哑人家庭的小孩,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影响,他们的手语都是自然状态下的聋人彼此交谈使用的手语。而聋校的健听人教师打的手语是手势汉语,它基本上是按照中文句子中的词语顺序逐词进行翻译。郑璇打了一个比方,“你叫什么名字?”这句话用手势汉语逐词比划,顺序是:你——叫——什么——名字。而自然手语的顺利则是:你——名字——什么。只有自然手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聋人手语,我们应该尊重它自身的规律。普通汉语的语法结构是主语、谓语加宾语;而自然手语则是主题加陈述的形式。因此自然手语更加简洁易懂,更适合手语者交流。
梦想起航:自我认同与融入主流
出于对手语的兴趣和热爱,硕士毕业后,郑璇了解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个言语障碍专业方向,研究中国手语语言学,于是2005年她成功考取了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成为国内第一个聋人博士。来到复旦大学的两年间,郑璇一边研究手语,一边走出校园,加入了上海残疾人艺术团,继续着她小时候的舞蹈梦。
“我从小就想学,六七岁的时候就趴在少年宫舞蹈房的窗口去看其他的小孩子跳舞。我父母觉得学习舞蹈会影响我的学习,不送我去学。我一直记了很多年,我觉得不能让它成为终身遗憾。”

▲ 独舞
中国民族舞和古典舞是她的最爱。亭亭玉立的身材,白皙的皮肤,看上去就是跳舞的料,跳舞培养了她挺拔优美的气质,她的男朋友更是开玩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金针菇”。舞蹈让郑璇逐渐变得更加自信,对舞蹈的热爱与日俱增,逐渐地也敢大胆地走上舞台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了,以前的她,性格难免孤僻不合群,自从开始学习了舞蹈,郑璇开始放开胸怀,大胆地与人交流,与朋友们共同欢笑,融入了朋友圈之中。
她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舞蹈。非常有舞蹈天分的她,虽然听不清音乐,但是靠听重音节拍,加上数拍子,郑璇进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跳过《千手观音》。
“我有两个兴趣爱好,一个是写作,一个是舞蹈,这两个都是对于自我的一个表达,当然现在我对写作的兴趣稍微要淡一点,因为现在我有比较畅通的渠道来表达我自己,我现在口语方面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很多,我现在可以说很久、说很多。”

▲ 和学生在一起
随着对聋人群体了解的增加,郑璇觉得自己应该为大家做点事情,尽量帮助大家融入社会。于是,郑璇博士毕业后,最终选择了重庆师范大学特教系当老师。当时重师大的特教系很小,两年招一次生,只有两个老师:“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重师大,重师大从2005年开始创办聋人的高等教育,有聋生,但他们现有的老师手语不好,特别希望我来,试讲的时候学校人事处和学院的院长等一些领导都来了,我用口语讲了一堂课,还是很顺的。”于是,郑璇就去了重庆师范大学。
郑璇在聋人教育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总结了很多经验。她觉得,聋人应该做一个双语者,或者双文化者更加适合他们心理的需要,如果单纯只沉浸在聋人的群体里,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是很狭隘的,如果把他们放在健听人的环境里去,不给他们适当的支持的话,他们也会特别的孤立,因此郑璇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在两个世界转换,“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也是希望更多的聋孩子像我一样,一方面既具备比较好的汉语水平,不管是口语能力还是书面语的水平,即使不会口语也可以笔谈;另外一个方面他必须拥有他的群体,知道他的文化,不怕承认他是聋人。”
在郑璇看来,双语、双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传统的聋教育是口语教学,但是在二十世纪末期,双语、双文化的理念开始涌现,它不仅仅是代表聋校的课堂教学法的转变,更是一种观念。是世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聋人群体只是一个少数群体,需要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和权利更多的尊重。
目前郑璇承担了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还做了学生工作,带了两个聋生班,2011年底评上了副教授,2012年评为硕士生导师,今后的工作会更加具有挑战:“我想工作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职业,应该是一个事业,因为我的兴趣放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在聋人的文化、聋人的语言、聋听两个群体的沟通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希望聋人能够真正和听人一样,是一个平等的群体,只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

▲ 在特教系会议担任手语翻译
【人物简介】
郑璇:女,湖北武汉人。1983年意外导致全聋。1998年,考入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2002年被保送为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5年考取了复旦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聋人博士,开始了对中国手语语言等相关问题的学习研究。2008年进入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教系执教,2011年升为副教授,2012年评为硕士生导师,现为特教系副主任。曾获“重庆青年五四红旗手”等光荣称号。郑璇爱好跳舞,虽然听不清音乐,但是靠听重音节拍,加上数拍子,曾入选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并参与《千手观音》,跟著名的聋人舞蹈家邰丽华曾经是同事。
【编辑随想】
我们经常在媒体里能够看到,很多聋人开口叫出一声“妈妈”,观众顿时泪下,也有很多家长为此将孩子送进语训中心,或许,这对于家长是莫大的安慰,但是,对孩子,意义大吗? 我们总是强势地认为发声才是表达的主要手段,却忽略了无声的表达同样是强音,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多种的,表达者内心的感受和愿望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注。
在各种关爱残障人的活动中,学手语无疑成为了一种热潮,只要举行大型残障人活动,必定组织志愿者学手语。要想做到健听人和聋人的交流,似乎除了让聋人说话就是让健听人学手语,学手语或许是容易的,但是听障者要想达到无障碍沟通的效果笔谈或许更能够淋漓尽至,关键是,众多志愿者学习手语的真正心理来自沟通需求,还是某种“参观”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