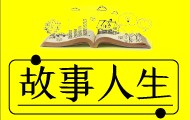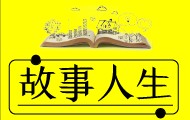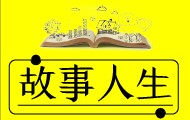【聋眼】杜晓玲:我不是生育机器
杜晓玲26岁,生活在华北农村。她有着多重残障——听力和言语障碍,还有轻度的心智障碍。
晓玲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大。因为晓玲是个女孩,又有残障,家人几乎不让她出门,就更别提让她上学了。“本来就是要嫁人的,又是个残疾的孩子,上学有什么用。”这是父亲一直以来的想法。晓玲一天学都没上过,整天跟着母亲做农活和学刺绣。她很有灵性,刺绣作品栩栩如生,也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但是家人总是说:“你不用出门,要钱也没什么用处,就贴补家用吧。”所以,每次在外卖了作品回来,晓玲都把报酬一分不剩地交给了父亲。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晓玲快要结婚的年纪。因为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为了给弟弟娶媳妇,父亲决定两家人换婚。而晓玲的换婚对象比她足足大出了二十多岁。虽说年龄不一定是影响婚姻的问题,但是,一位残障女性就这样进入一段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她的生活状况如何,似乎也可想而知。
婚后,晓玲依然会去集市卖自己的刺绣作品。这些收入在每次回家后都会被丈夫拿走。因为婚前也是把钱交给父亲,晓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即便如此,丈夫却依然会觉得挣的钱太少。丈夫最初只是用眼神表达不满,后来开始训斥她。虽然晓玲听不清他说的,但从他那狰狞的表情中,她能感受到丈夫的不满与气愤。
婚后没几个月,晓玲怀孕了。因为身体原因,家人让她暂时在家养胎,由此她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在丈夫和婆家人看来,她每天在家,没什么需要用到钱的地方,也不给她任何生活费。孩子出生后,晓玲又开始刺绣卖绣品来挣钱养家,但是丈夫已经不满足这些收入,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对她动手,晓玲身上也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
在晓玲生活的村子里,有一些孩子多的家庭会将新生儿卖出去赚取收入。晓玲的孩子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就被丈夫带走了。一开始晓玲以为只是暂时到亲戚家,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孩子回来。接着,第三个孩子也这样被丈夫带走。晓玲是后来在和邻居们的聊天中,隐隐约约觉得孩子被卖了。在巨大的打击之下,晓玲质问丈夫。但这却给她带来了更严重的家暴。暴怒的丈夫对她又打又骂,还说她的刺绣“做的那都是什么不值钱的玩意,能赚几个钱?你也就只剩下这点价值了,当然要好好利用。”晓玲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当成生育的工具,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当作物品一样贩卖。
对于晓玲的处境,娘家人没有站出来帮她说话,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周围的乡亲也习以为常,甚至还会在晓玲大着肚子时问她“这是第几个啊?上一个卖了多少钱?”。
《反家暴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都有强有力的条款,《刑法》也有具体的规定,但是这样的悲剧还是屡屡发生着。这也是我们想要通过一个个的案例故事告诉大家,残障妇女作为最弱势的群体,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看见,她们的生活需要被认可与尊重。
点评:晓玲的故事令人震惊。因为多重残障,她被自己的原生家庭和丈夫家认为没有价值,尽管她会做农活,刺绣也好。她遭遇了多重家庭暴力,当物品一样被给弟弟换媳妇,经济剥削和控制——挣的钱不是被父亲就是被丈夫控制;不仅挨骂挨打,而且沦为生育机器,所生孩子也成为直接遭遇暴力的受害者——被贩卖。晓玲的故事也揭示出精神障碍女性面临着无法掌控自己生活的困境。更令人唏嘘的是,因为歧视和偏见,家人和邻居等周围的人也认为她应该承受这样的命运,对暴力容忍和默许。现在,我国有了《反家暴法》,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晓玲这样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权利有了新的保障。村委会、残联组织、妇联组织不能再对晓玲遭遇的暴力视而不见,而有法律义务报案,或者可以代为申请保护令;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有所作为,保障晓玲和她的孩子免于暴力的权利;如果这些机构不作为,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