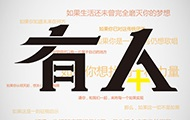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说媒】封面故事:漫漫盲生路,总会错几步
我们关注的不是残障,而是最真实的人性,最温暖的人性,最高尚的人性,是那个抛开标签,还原真实的“人”。
2013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本刊的出品方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发布了《2008年至2012年中国印刷媒介残障报道观察报告》。研究表明,在2008-2012年的1468篇报道中,报道主题大都集中于残障人残疾本身及其健康或康复方面,忽略了报道残障群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等重要方面;残障人群的形象多被呈现为沉默的“客体”,且少数报道将其视为“社会负担”或“可怜的人群”;大多数“帮扶”新闻和有关家庭、企业或社会支持的报道局限于“献爱心”或“孝心”,缺少从权利视角对残障人群的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关残障人群就业、职业发展、工作表现的报道较少;亦缺少残障人群参与公共事务的报道;尽管中国有75%的残障人口生活在农村,但有关中国农村残障人的报道不超过10%;此外,消息来源有较大的局限性,极少有消息来源于残障NGO或残障人士,多数新闻报道也未能结合报道案例向公众介绍有关“无障碍”、“合理便利”、“通用设计”、“残障人群的权利”、“基于残疾的歧视”、《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保障法》等重要知识。同期还发布了《2013年度中国十大残障权利事件》(其节选版已在2013年第四期《有人》杂志中登出)。
此两份报告的出炉,自然引来了媒体的纷纷报导。这也是报告的发布者乐意见到的情况,只有传播,报告才能够被更多人阅读,并可能受到影响与改变。
翻开第二日的媒体报道标题,关于观察报告,媒体报导的标题,大多类似于《社科院报告,路灯不亮称瞎子,歧视残障者》,关于十大权利事件,媒体的标题则大多是《2013年中国十大残障权利事件出炉,首都机场爆炸案在列》。与我们预期的深入讨论不太相符,未免有些气馁。
不过该新闻在微博中发布后,引发的讨论却挺多。当有人在反思,有人在争辩时,有人这样评论:
“社科院更该研究盲人为啥不能高考。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充分保障残疾人的其他硬性利益。也就是说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其他利益都得到保障了,我们再来纠缠这些细枝末节。话又说回来,尊重残疾人,也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我看社科院更该关注的倒是这盲人为什么不能考大学的事情。”
作为该报告课题组的成员,同时作为一名视障人,我在看到这则评论后,开始了梳理与反思。
从十岁就要考虑养老的故事说起

我在10岁时因药物性青光眼,导致视神经萎缩,视力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到不足0.1。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戴上眼镜没啥用,趴到书上能看清书本上的字。按现行的标准,不说是一级盲,至少也是个二级盲。但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原来我已经划归了“残疾人”,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对于“残疾人”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偶尔见到的肢体障碍者和心智障碍者。对于视障人的概念,就是全盲,对于听障人的概念,就是一点都听不见。因为媒体上的报道开头,从来都是“他们生活在黑暗的世界和无声的世界里”。
起初,家人自然是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从号称失明数十年的人都治好的日本归国博士,到深山老林里隐世不出却名传千里,吹口仙气就能残灯复明的老神仙,他们各种摇头,各种无效,各种“这辈子就没希望了”的断言,让我们慢慢绝望,放弃。彼时,家人的内心充满绝望,他们只当我这辈子已然是完蛋大吉。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自然是他们过世后,我要如何孤苦无依、穷困潦倒地了却残生。是的,十来岁的小朋友,家人带着对我的爱,和对盲的绝望,开始为我计深远。
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就是准备生二胎,理由当然是将来能够有个人代替他们照顾我。但是,据我奶奶回忆,那时的我十分激烈地表示了不同意,生怕他们有了另外一个“正常”的孩子,就会将我这个“不正常”的孩子冷落或者抛弃,并以“如果他们敢生,我就将之掐死”为威胁。他们只好作罢。
可奇怪的是,对于此事,我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分析,估计是后来意识到了我这种自私而狭隘的想法对他们是多大的伤害,内心愧疚,潜意识选择了将之遗忘。现在再分析为何当时我的反应如此激烈,恐怕是深深地认为自己已经是废物了,要是再没人管我,那才是要孤苦无依地度过下半生。这种对于“残=废”的恐惧,源于不了解,源于健全对残障的想象,也源于很多媒体界的塑造。
身残志坚,是不是转机?

说实话,我当时就一十来岁的小屁孩,除了知道学习,鲜有独立思考,对于“盲”这件事情信息来源也仅限于媒体报导与口口相传的可怕,心里确实难以接受,但更多的是不愿意去想。那么逃避的办法就是,强烈地要求我要上学。对于“盲”也只有绝望认知的家人,思来想去,也无他法,决定托托关系,把我先送进学校混着。就算是养老问题,那也还有好几十年,关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至少当时得有个事打发时间吧!
岂料,走进初中校门的我,第一次月考就大放异彩,不小心考了个全年级第一。一下子,我就成为了全校关注的焦点。从那时起,“身残志坚”就成为了我在被人提起时,形影不离的小伙伴。
刚开始,我确实洋洋自得,大会小会,接受各种与我有关无关的表彰,譬如三好学生;四敬好少年;自强不息标兵;也不管眼睛发不发炎,开会肯定要发言,分享一下我作为一个坐到讲台上都看不清黑板、按理说就应该是啥也不能的人,是如何地热爱着学习,是怎样地克服着困难。
每当老师在各种场合向同学们说“人家蔡聪眼睛都这样了,学习还能这么好,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时,我都会故作羞涩地低下头去,心中却在一阵又一阵的小激动。至于不用上体育课、不用打扫教室卫生,这是特权,是可以拿来炫耀的特权。
再回首,当时的我还真像一个屌丝幻想着升职加薪担任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不过屌丝总有梦醒的时候,现实真让人难以接受。
No与Why

一年又一年,渐渐我开始对汹涌而来的表彰与夸赞麻木,与惶惑。眼睛看不清,未来不光明,被掩藏起来的问题再度浮现。当老师们再拿我看不见都能学得这么好来教育其他同学时,我仍然会深深地埋着头,但这时,心里只有抗拒与无助。
有时候我也想和同学们一起上体育课、跑步、踢球,接受女同学们的欢呼与鼓舞;我也想加入大家做卫生时的嬉笑打闹,而不是傻傻地站在走廊上无所事事。我想告诉大家,我看不看得见,与学习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在那些完全不在乎我和他们女朋友貌似亲密的家伙们的脸上狠狠揍一拳。
但所有人的答案都是:No!所有人的脸上,永远都对我,洋溢着温暖。
“你看不见,怎么能跑步呢?万一跌倒了怎么办?”
“你看不见,怎么踢球?”
“你看不见,哪扫得干净?”
“你看不见,还是别弄了,我们这是照顾你。”
“喂,我今天和我男朋友又吵架啦,陪我聊一聊!”
……
我的脑袋里仿佛有无数个人在说:“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我开始变得暴躁,在老妈没有及时赶回来给我做一顿饭时;在亲友们围坐书桌打着麻将我却只能呆坐一边时;在放学后校门口汹涌的自行车流中……我什么都想要,我又什么都讨厌,我怨恨我的看不见,我怨恨我的什么都不能!
直到有一天,我因考试成绩非常糟糕,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你最近怎么搞的,怎么成绩下降了这么多?”
班主任的语气很严肃,很认真。我相信,在那一刻,她绝对没有想到我看不见,理所当然地应该考不好。我低着头,瞬间热泪盈眶。
她觉得我应该能做到,她觉得我应该能做好。也许这是我之前的表现给她的印象,但至少,她没有先帮我找好借口与理由。
我要是说,在那一瞬间,我猛然醒悟,明白了我究竟要的是什么,领悟到了天将降大任于吾,那我这个快要三十的老男人面前肯定坐着一个志愿者小妹妹。一个青春期的小屁孩,请原谅我再次使用了这样很不尊重儿童平等权益的用语,我只是想说,那时的我,连老盲分几级都没搞清楚,自己都还在歧视着残障人,能懂个什么!更甭提像美国女诗人玛雅·安吉鲁,她是位黑人,那般浩瀚与深沉地思考:
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Yes

在无数个No,与班主任的这一个Why之后,我开始琢磨,我应该如何获得我所要的。尽管当时还没建立起指导思想与理论体系。
小伙伴们想踢球啦,那我就凑上去,我掏钱买球,你们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带我?随便把我算在哪队里,不计入人数成不成?多个人,当肉盾也好对吧!
小伙伴们想出去玩,可又怕家长盯着,没关系,来我家,我学习好,全校都知道,来来来,说是上我家学习来啦,我给你们做伪证,那玩啥子总得带上我吧,溜冰、打台球、玩扑克、打电玩、玩赛车模型、看VCD、唱KTV……
只要能带上我,就有机会让大家了解我,也能在了解之后,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如何让我也能参与进来。
比如在足球上套个袋,比如在踢球时大家多喊一喊,比如买来数字比较大的扑克,比如边看碟边给我讲解……
直到后来,我的视力再次下降,降到了0.01,这回连书都看不了了。好在那时候我已经混过了中考,尽管因为视力原因,理综考试的答题卡没能填上,但仍旧混入了一个不错的高中。
在那里,我仍旧用着这些套路,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他们愿意帮我念课文、念作业,因为他们只需要动动嘴,答案等着我就成。他们也喜欢为我读书,反正我掏钱买,谁喜欢看哪一类,我都了如指掌。而也是因为我成绩好,老师也愿意在考试的时候为我读题。
要说有遗憾,那就是早已不再懵懂的我那颗骚动的少男心,总是无人理会,看着男生女生上课纸条传情,担任信使的我心中很是酸楚。只恨当时如果有智能手机和屏幕朗读软件,哥也不至于孤苦零丁,望女兴叹这些年。
未来,似乎全是Yes!
梦想照不进现实

一切美好,如梦幻泡影,在高考面前都被秒杀。当我从老师那得知,我提出的高考时找人念题的申请被拒时,我正兴冲冲地和同学们吃完火锅回来。坦白讲,我早已记不得当时被拒的理由具体是什么,这些年工作中接触到了许多申请各类考试无障碍的案例,大家和我这“苦主”得到的回复都差不多。
不是没有法律,不是没有技术,但就是有理由拒绝。现实如此,我无力反抗。因为当时的我,也这么认为,谁让我看不见呢,干什么都需要给人添麻烦,人家帮你是人情,不帮是本份。因此,没有像第一期《有人》杂志里的宣海那样一路抗争,也没有像媒体里火起来的盲人高考第一人那般呐喊,我这个高考已经报上名的家伙,默默地收拾起大学里学中文的憧憬,蹲回家中,和突然间又开始心急如焚的家人一起,四下打探。
还别说,在那本最畅销的家庭杂志里,我们看到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孩艰难地用放大镜学习,考上了一所盲人高等学府——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老爸赶紧打电话到杂志社去索取相关信息,又托人在网上查,我们全家此时才了解到,我原来已经是个盲人。可以考长春大学,但得先办残疾证。人家考试有汉字试卷,也有盲文试卷,像我这样的,恐怕得赶紧学盲文。
学盲文,学盲文,那得找盲校呀!噢,原来还有盲校,在哪里,在哪里?好一通鸡飞狗跳,我们找到了当地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那里,有六名盲人学生。我算是正式迈入了盲人们生活的“黑暗的世界”。
那时是2004年下半年,我在普通学校读高三,离我残障已有9年。
原来,这就是黑暗的世界

在那里,我头一回接触到了盲人,发现他们多才多艺,都是音乐天才,他们有的弹钢琴,有的吹笛子,有的拉二胡,让我赞叹。在那里,我同样知道了,原来我花800元报名一个月学习的盲文,就是一组凸点的排列组合,代表不同的拼音。实际上第一节课我就完全明白,接下来需要的只是熟练。在那里,我还知道了,原来电脑上装上一个叫屏幕朗读软件的东西后,就可以说话,就可以让盲人跟健全人一样操作。
随着我顺利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接触到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盲胞,让我意外的东西越来越多。
原来盲人不是个个天生都音乐天赋好,只不过是在盲校里没有升学压力,素质教育推行得好,大家大多会学样乐器傍身。但同样也有五音不全的。
原来盲人不是看不见了,就生活在了黑暗的世界里,对世界一无所知。只不过是和用视觉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人有所不同,盲人依靠的是听觉、触觉、嗅觉,还有感觉。
原来盲人能够用的电脑屏幕朗读软件,其中流行的一款,是由盲人程序员开发的。
原来,盲人即使看不见,拿起盲杖,自己一个人同样能去很多地方。
原来,盲人也不是只能做按摩。
……
原来,盲人,不是我之前很多年想象的那样。
原来,看不见,只是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同,没有,也不应该有高低。
后来,我毕业了,不想做按摩,原因有很多,但同样并不伟大,也不深沉。我知道了这么多原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原来,我想找到答案。
我们,一直是他们眼中的我们

2010年夏天,我来到了北京,加入了一加一,也就是我们这份杂志的出品方。这里,有一群残障人。这里,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里,逐渐给了我答案。
残障,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除了环境的障碍,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误解与负面态度。人们在很多时候,认为伤残者是无能的,是需要被同情的,是不正常的,是需要被纠正的。正是这些认知,才有了我那些年的经历与困惑。而人们这样的认知,究竟从何而来呢?
是残障者给了人们这样的印象,还是人们先有了这种想象,将残障者牢牢地隔离与限制从而加深这种印象?是残障者将自己隔离开来,还是因为人们的态度与做法,使残障者被隔离?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过,无论源起如何,大众媒介正在不断地加深残障者在人们心中旧有的刻板印象。
翻开各种媒体,对于残障者的报道,似乎和二、三十年前没有太大区别。主流仍旧是身残志坚与大爱无疆。身残了要是志不坚,是不是就只能玩完?大爱是社会文明进程的需要,但是不是没有大爱,也不能再指责些什么呢?何况,这样的报导,背后的框架,仍旧来源于认为残障者的无能与不正常。
就像我当初视力下降后,家人的恐惧、无助、绝望。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医生们,从来都是说,要努力地把这点光保住,否则这辈子就完蛋了。可我曾经采访的美国聋盲人Haben告诉我说,在美国,医生在遇到无法治疗的视障者时,会告诉对方及家人,这没有什么,接下来你们应该去训练中心,去学习适合你身体状态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人生,很多视障人的人生,是不是就会是另外一番光景呢?至少,我的家人,不用那么早就开始担忧我的“养老”问题了吧!
还记得2013年平安夜,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坐在一起,和她的腿聊天时(编者按:见《有人》杂志第四期《对话》栏目),她曾说,如果不是她在伤友论坛里看到了好多人生活得多姿多彩,如果不是受到了他们解决困难消除障碍的启发,在他们幽默风趣、乐观积极的态度感染下,她不可能那么快接受自己截肢的现实,更难以鼓起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为什么我们的医生不能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无法提供最适合的指导?为什么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面对残障,只能恐惧与绝望?是谁在让他们如此认为?
可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那么,谁有责任让他们知道,谁有责任让他们了解呢?这个还真没法说。至少,我觉得,作为残障人,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有责任去做出改变。
因此,我们关注残障儿童的融合教育,希望大家在小时候就能够彼此了解,不再大惊小怪;我们关注视障人的高考无障碍,希望视障人同样能够接受不受限制的高等教育,而不是被局限在一方按摩店里。而我们,同样也关注大众媒介对残障者形象的刻画,期待大家逐渐意识到残障者的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
如果人们在提及残障时,不再觉得残障就是人生幸福的终结,而认为接纳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好比在语言陌生的国度,你就像一个言语障碍者,在黑暗的环境里,你就像一个视力障碍者一样,我们把目光投向如何消除障碍,如何提供辅助与支持,让其能够独立自主地生活。那么,会不会就不再恐惧与绝望了呢?
我曾经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反对媒体使用“打老婆”这样的词语,也觉得她们面对新闻报导中“党政机关干部要坚决抵制金钱权利与美女的诱惑”中的“美女”一词过于耿耿于怀。也许是因为我是男性,也许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男权中心的环境里,所以不以为怪,反而觉得她们过于敏感。但回想自身这些年的经历,当残障者生活在以健全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社会中,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推己及人,算是有了些体会。因为,那些负面态度,都潜藏在人们的无意识里,而无意识的表现,就是这些言语与框架。它们深深扎根人们心中,筑就了一道道高墙,将少数群体排斥、限制、隔离。投射到残障者身上,就是恐惧与无能,错误与不正常。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时,也就是情况开始转变之机。
因此,我们讨论应不应该与必胜客虾球广告较真(编者按:见《有人》杂志第二期《对话》栏目),我们推动关于大众媒介中残障人形象的研究,我们在杀死纸媒的时代还要创办一本杂志,来做我们的媒体。
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正是因为明白了这样的思考的伟大,所以我们的杂志才叫《有人》。我们关注的不是残障,而是最真实的人性,最温暖的人性,最高尚的人性,是那个抛开标签,还原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