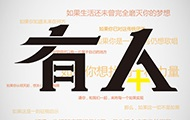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残障好声音】专栏:依然张海迪
 前段时间读刘瑜的《观念的水位》,看到这样一个观点,读后顿觉恍然,对近几年来的一些“奇怪”现象不再惊怪。刘瑜在书中写道:“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前段时间读刘瑜的《观念的水位》,看到这样一个观点,读后顿觉恍然,对近几年来的一些“奇怪”现象不再惊怪。刘瑜在书中写道:“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确实,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尤其是2010年过后,八零后们奔三了,有的在逃离北上广,有的想回归体制内,更多的人,在这个社会阶层流动逐渐板结化的社会里,只能生活在夹缝中,梦想难以照进现实。我们三十难立,三十不立,但我们看待自身、看待社会的观念却渐趋成熟,水涨船高。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Jean M. Twenge写过一本《Me世代:年轻人的处境与未来》,书里所谓的“Me世代”,指的是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美国人,作者认为他们的特质是:高度自尊、外控性格、高压生存、平权意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就这个特质的描述看,我们曾经初生牛犊,个性张扬;我们现在生活尽管纠结,却也开始沉静,努力做着能够对阶层板结的社会做出的抵抗,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过往的怀念。《李雷和韩梅梅》、《老男孩》、《春天里》……一幕又一幕,承载的都是曾经的最美。但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过往的精神领袖,也在我们观念“水位”的升高中,开始经受更大的风浪。这里面最让残障人揪心与关心的,是我们的残联主席张海迪。
她的事迹不再赘述,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给予她两个美誉:“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由此,她成为那时中国最轰动的“励志人物”。
可以说,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乃至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在张海迪的励志故事中成长起来的。还记得十来岁时因病导致视力障碍严重,在家里和学校,处处都有人与我讲张海迪的故事,每当我情绪低落时,就有人以她来激励我。当我取得一点成绩时,则又有人以她来赞誉我。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前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应该是我们实质权益上的领袖,但张海迪,却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2008年11月13日,张海迪当选新一届中国残联主席。作为曾经的平民偶像、残障英雄,她的上任,应该算是实至名归。当我们期待着她继续为我们中国近亿残障人指明方向,带领我们奋勇前行之时,她却身陷于各种指责与质疑的泥淖中,和“雷锋”这个精神符号一起,在很多人心中崩塌。
先是有人在网上爆料说张海迪为德国国籍,后她的国籍又跑到了日本;接着又有人指她微博中有跷着二郎腿的照片,怀疑其为假残障人;引发最大波澜的则是2011年6月不少网友在其微博中留言,希望她关注其盲人同乡陈某某的境遇,但她却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之事,一时间,各种责问汹涌而来;后来对巨额残保金去向的追索与质疑,也落到了她头上。而这位平民英雄自学成才、多国语言精通的励志事迹是否真实,在种种剖析中,也像“雷锋同志做好事从来不留名,他只写在日记里”一样,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面对这些诘责,海迪大姐有的做出了解释,譬如她在微博中表示,跷着二郎腿是工作人员辅助,那样有利于分解脊柱力量,能坐得更久。至于她的国籍,能够成为十八大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但面对一些指责和更多责任担当的期望,她保持了沉默。
网络舆情如此,让笔者一时间有些恍惚。可当有人跳出来指责大家“怎能对一名残障女性如此凶残”、“怎能对曾经的精神领袖如此贬损”、“怎能失去内心的道德底线”之时,笔者又颇不以为然,终在《观念的水位》里找到了答案。
其实,张海迪,或许依然是张海迪,只是这几代人和这个时代变了,我们观念的“水位”变了。伴随这个水位一起变化的,则是“残障”的概念与残障权利运动的历程,还有我们残障人的需求。

在张海迪成为“张海迪”的那个年代,笔者同样看到,1981年,也是联合国国际残疾人年,中国原邮电部发行了编号J-72的纪念邮票,全套一枚,票面上写着“国际残废人年”。在此之前,对于残障的认识就是“残废”,充满了歧视与否定。当残障人在邓朴方的领导下提出“残而不废”的口号之时,自然也需要“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偶像,成为精神领袖;这个领袖来自民间,是位女性,更具传奇色彩。同时,那个时代需要知识明星、运动明星,他们坚强、勇敢,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内涵,这样的道德形象更符合当时中国人的需求。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摒弃了“残废人”的提法。“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神话与传奇,一个接着一个,成为媒体宣传残障人的主流。在当时,对正努力从“残废”中挣扎而出的残障人来说,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慰藉。
可二十多年过去,沧海桑田,早已换了人间。当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之际,也恰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批准实施之时。残障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自己的教育、就业、出行、婚姻及参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权利与机会均等,我们早已不满足活在他人异化、排斥、怜悯与歧视、还甘当于精神世界里的“巨人”的环境里。近几年来,《残疾人保障法》进行了修改,《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颁布实施,残障人一直期盼《残疾人教育条例》的出台,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了履约报告,更有本土残障人自组织公开递交影子报告,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中,发出残障人自己的声音……
一件一件,一桩一桩,都显示着:我们观念的水位,涨了。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就像老师体罚学生、城管追打小贩,我们从“不以为怪”到“无法容忍”;就像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更适合她的地方应该是讲台,而不是残联主席的“宝座”一样。
博客与微博中的张海迪,依然那么柔弱与善良,依然带着文艺与敏感。被供上庙台的她,尽管在试图做好自己的人大代表,却赶不上我们水位上涨的速度,但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残障领袖,已不再应该只是一个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