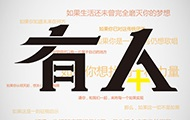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看见】2020年残障新闻盘点|残障不在隐秘的角落 - 盘点七
盘点7:机构化的命运
关键词: 院内感染,合谋诈骗,护工涉嫌强奸,自闭症儿童虐待案重审
残障者居住机构走向隔离的迅速发展,要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生物医学的发展,西方社会快速都市化与工业化,这些都为用隔离的方式照顾、治疗、监禁各种类别的残障人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1]。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机构式缺乏人性的照顾机制”越来越被关注,也是西方的“去机构化运动”的开始,这一运动同时与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各地区与国家进行。我国尚未经历大规模机构化安置残障人的高峰,但住宿型的特殊学校,日托、全托的心智障碍者康复机构增长十分迅猛,加之第一代走出来倡导心智障碍者权利的家长们逐渐年迈,为解决现实问题,他们也在提出“星星小镇”这样的集中安置心智障碍者养老的模型。

(摄影:《三月风》记者王雨萌、白帆)
2020年发生在机构内的集体感染、纠纷与犯罪事件,在疫情这个背景下,给了我们提醒,让我们去思考要不要走向大型机构化的老路。然而,这种情况下对机构化的审视,和国际上以消除隔离和实现社区融合为目标的去机构化完全不是一回事。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院内的集体感染,可能只是个案,但确实提醒我们,封闭式的机构,对残障人权利保护的威胁和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而当上海某残联与福利院工作人员合谋诈骗残障老人房产的新闻被曝出,讨论的面向就已不仅是服务提供者和监护者的道德问题和犯罪行为的惩处,还应该要通过这起事件如何能够被发现,去反向追查这类事件的普遍性和机构看护模式里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针对河北魏县男性护工与女性精神障碍者发生性关系并致其怀孕的事情发生,关注不应陷入到是真爱是诱骗是其它什么的罗生门里,而要看到医疗、养护机构里的不对等权力关系和服务提供者的职业伦理。
相较于权利与规则,在我们的文化里,更习惯讲人品与道德。加之传统的个人模式在看待残障时,讲求的就是医疗的绝对控制和同情怜悯为基础的帮扶与照料,在个人奉献的服务提供者,在努力“纠正残障”的专业人员,在帮助社会和家庭减轻负担的的照料者,他们的行为很难被质疑,也缺乏相应的程序进行监督。一如引起争议的重庆女博士的“厌恶疗法”[2],家长们可能只会看到孩子的问题行为消失的效果,而不会从残障儿童的权利和身份特性的角度来意识到这是一种虐待与不人道的对待方式。只有在如2016年广州某机构一位自闭症儿童在19公里拉练后死亡[3]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时,才给了家长和社会以一时的阵痛,关注机构为“治愈“残障而行的虐待行为。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高于他人的注意义务强加于家长,还是要回到提供康复、医疗、养护服务的机构的管理上。2020年3月这起“自闭症儿童疑遭康复老师虐待案重审,被告人获刑一年九个月”则令人振奋,尤其报道在列举证据时强调当事自闭症儿童的恐惧感受,和因语言障碍难以表达的处境,就是只关注问题行为是否得到修正的家长与社会最易忽略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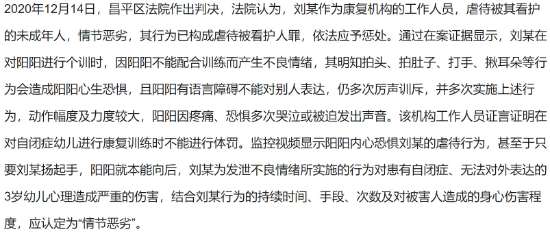
韩国作家孔之勇在其根据真实事件撰写的小说《熔炉》里,除了描绘出听力言语障碍人士在隔离的学校里惨遭欺凌却无法发声的现实之外,更是给了我们以更多这种生活在机构里的被照顾者“无法发声“的隐喻,这不仅仅是有没有监督的问题,而是如果社会一直用疾病与缺陷的视角看待残障,以修复和纠正的方式来对待残障,那么肩负着社会训练与养护之期望的隔离式的机构,随时可能滑落向深渊。
也许家长会跟媒体说,你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你们不明白家长的绝望。但残障的专业让我们有义务提醒,即使妥协于现实,选择了机构,或者有信心从《公约》的原则出发,自己能建设一个理想的机构,也切莫在将残障人送入机构那一刻,觉得卸下了重担。机构有其价值,有其专业,但应是在残障的社会与人权模式指导下,成为残障人参与并融入社会,获得有品质的生活的支持者,其中之一。
参考资料
资料: 详见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编,《障碍研究:理论与政策应用》,第一章节,西方障碍与文化巨流,2012。
[2]资料: 欲了解事件详情,可阅读相关报道:女博士“以暴制暴”治疗自闭症儿童,10人回归正常,重庆商报,2014-07-11,
原文链接:https://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7/11/37283416_0.shtml
资料: 欲了解事件详情可阅读相关报道:3岁自闭男童死在康复基地,南方都市报,2016-05-04
原文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6-05/04/content_33304.htm#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