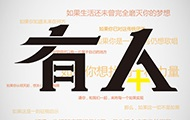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低视利】机遇还是挑战,看你怎么看
残障不一定是被动状态,正好相反,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主动状态来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我的大半辈子是在回避残障中度过的。虽然是先天性低视力,小时候因为眼病也忍受过n次手术,但从未觉得自己是残障人,感觉“残疾”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在英国和南非上学很自然就上了普通学校。那时候还没有人谈到什么全纳教育、融合教育之类的,大概只有全盲或者最严重的低视力者才上盲校。学校也没有专门为我提供什么合理便利(那时候还没有人用这个词汇),不过有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有些激烈运动我不能参加(说实在的我也不在乎,因为不大喜欢踢足球),所以老师让我在操场上跑步或者呆在图书馆读书。
像很多不接纳自己的状态的人一样,我也比较善于“装明”,但有时候实在看不清黑板我还会露怯。最尴尬的是老师让我念课本的时候我看不清就结结巴巴地念出来,有的老师不知道我低视力还以为我有学习障碍。尽管如此,我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回避我是低视力的事实,不认为自己是个障碍人士。
现在回想,我来中国学中文与视力不好并非无关。低视力在我少年的心里无疑产生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我从小比较爱独自思考问题,虽然不躲避人群,但也不大合群。青春时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但由于参加不了很多“正常人”能参加的活动,我就发现了另一种方法:我开始自学中文,对既遥远又神秘的PRC产生了兴趣。
70年代中国还很封闭,西方人学中文的是极少数,所以这又给了我一种自我认同。说实在的,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视力还不错,还能到处骑自行车(当然那时候汽车少,比现在安全得多,而且加入马路上不慌不忙的自行车队伍让我感到很安全),但是北京的灰尘老让我眼睛发炎,而且过去发生多次的网脱总给我一种危机感。
尽管如此,我是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以后才开始注意到残障人的。这无疑与我视力逐渐下降,不得不考虑另一种生活道路有关。不过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到残障人的存在也不完全怪我,在中国,残障人,尤其是盲人,几乎是一个看不见的人群。第一次遇到中国残障人是在上大学时,当时我每周到附近的林业大学教英语,有一位外语系教授的儿子是肢体障碍者。这位坐手摇轮椅的二十多岁年轻人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家自学英语,水平很高。那年,他和他的父亲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十分敬佩他们。很遗憾我后来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后来我在陕北农村拍纪录片时,顺便问了当地的政府官员本地有多少盲人。他们对我的问题似乎有些惊讶:“我们这里从来没见过盲人,陕北人的眼睛好得很!”这个说法和我亲眼目睹的情况产生了矛盾,因为我在陕北见过那些盲人丧葬队和盲人秦腔木偶团。几年后我在内蒙、山西等地开始调查视障者的情况时,发现残障者为“隐蔽人群”是普遍现象,恐怕还不止于这些地方。
15年前我的视力开始明显下降,后来做了白内障手术又恢复了一些视力。然而,不愿意直面视障,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更多障碍。比如说,每次和纪录片摄制组拍片时,我总想方设法隐蔽自己的视障,生怕人家知道了我的情况,会觉得我不可以做电影工作。我自以为考虑得很周到:每次约人时,我一定会提前几分钟到场,站在那里等人来找我,而不要像盲人那样模模糊糊去找人还有可能找不到。现在想来,大家一定很清楚我的眼神不太好,但并没觉得它影响了我作制片人的工作。不过根深蒂固的消极意识总让我非要扮演“正常人”的角色不可。直到我开始踏上残障人权益工作的道路,我才逐步认识到残障中的“障碍”主要是意识中的障碍,而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伤残。
过去在中国当过老师,也拍过纪录片,低视力做这些工作总让我感觉是在顶风而行,想要取得进展很是困难。怎么能顺风前进呢?

1998年我在中国和英国认识了几位从事视障者教育的朋友,这使我开始琢磨残障、社会和个人命运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我越来越注意到那些被改革开放遗忘的人,或者说是中国的“弱势群体”。我曾有一位好友小陈,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只能拄双拐,行动不便。他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靠自学写作和绘画成为了有才华的艺术家。他充满了理想,梦想徒步周游世界,但坎坷的生活经历最后使他坚持不下去,生活状况越来越差,后来不幸提前离开了人世。小陈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开始意识到不让残障人发挥自身的潜能不仅会导致个人悲剧,对社会也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认识了更多残障者之后,潜移默化中,我寻找到了新的使命。
2002年我有机会为BBC广播公司制作介绍中英残障人生活的系列节目。从我接触的中外残障者中我明显感觉到,残障不一定是被动状态,正好相反,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主动状态来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英国一位视障朋友Ellen Bassani, 教我如何把残障视为自己的“优势”。她说残障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要包容它,不要回避它,要使它成为新的力量。我邀请Ellen来中国和其他视障朋友分享她的经验,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残障人多数有着共同的思考,因此残障议题可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了!
最近十多年来,我开始在中国从事促使残障人自我倡导的工作,争取协助残障人树立新的话语权,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国土之间建立桥梁,使所谓的“障碍”被视为机遇和挑战。有人说改变视角可以改变世界,甘地还提倡:“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我相信这样的理念对残障人的赋权具有深刻意义。
在以后的专栏中我将探索残障人平等意识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