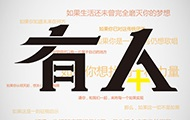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盲路】视力障碍的“蝴蝶效应”
故事要从我研究生毕业前的一次求职经历说起。那天我前往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面试任课教师的岗位,能够站在象牙塔的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一直是我的职业生涯目标,但无奈大学招聘教师一般都要求博士学历,仅有硕士学历的我只能先去这所职业技术学院碰碰运气。负责面试的是一位主管人事的副院长,他不出意外地提出了与我的视力相关的一连串问题,我也赶紧轻车熟路地把“电脑读屏软件能够帮助我无障碍地阅读和书写”的“神奇功能”向他娓娓道来。也难怪我对读屏软件这一“伟大发明”的介绍如此烂熟于胸,因为他在我面试经历中的出镜率远高于对我专业背景、学术能力和职业规划的阐述。
此时,那位副院长突然问道:“上课的时候学生在下面玩手机你能发现的了吗?”我顿感不妙,别说学生在下面偷偷玩手机,即便是在我面前光明正大地玩手机,只要不发出声音我恐怕也发现不了呀。
好在我反映还算迅速,在给出否定回答的同时,振振有词地向他解释一位教师只要讲课精彩自然能吸引学生认真听讲,否则即便发现有人玩手机任课教师恐怕也无能为力,甚至搬出了杨佳、富明慧等人的例子来力图证明发现不了有人玩手机并不妨碍视障人胜任教师这份工作。
然而,一切的解释和论证在这位副院长完美的逻辑推演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发现不了学生玩手机的人肯定维持不好课堂纪律——维持不好课堂纪律的人肯定上不好课——上不好课的人肯定胜任不了教师这份工作。--于是,他的结论产生了,连有人玩手机都发现不了的视障人是不适合当老师的。
尽管对于这次面试的结果我早有心理准备,但从“发现不了有人玩手机”推导出“不适合当老师”的逻辑思路还是让人感慨良多。
我也由此想到了气象学中的一种现象——蝴蝶效应。对于蝴蝶效应,最为常见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在两周以后导致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那位副院长的逻辑与蝴蝶效应何其相似,“视力障碍”是那只小小的蝴蝶,“发现不了有学生玩手机”成了蝴蝶煽动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变化,而胜任不了教师工作则是那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德州的龙卷风。
在气象学中,我想即便是最早提出蝴蝶效应的罗伦兹本人恐怕也不会真的相信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要仅仅归咎于亚马孙丛林中的那只蝴蝶。但在我们身边,对于视力障碍的“蝴蝶效应”坚信不疑的人却比比皆是。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中,人们提到视障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各种灾难化的联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视力障碍已经成为无能、累赘和悲剧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视力的障碍必然意味着某些能力的欠缺乃至丧失,从而理所当然地否定视障人从事某项活动的可能性,并据此为残障歧视寻找正当化的依据。在教育领域,声称视力的障碍会导致难以适应普通大学的学习生活成为拒绝给予视障学生公平的高考机会的重要理由;就业领域,公务员的招考部门可能仅仅因为视障人无法首先看清来人或者单纯的眼睛外观异于常人而实施了歧视性的体检标准并在公务员考试中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社会上,银行会把视力障碍与缺乏偿还能力相联系而拒绝给视障人发放贷款或办理信用卡,保险公司常常把视力障碍与较高的事故率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视障人排除在适格的被保险人之外;生活中,视障人的父母可能从“视力障碍”联想到“毕业了也不好找工作”,从而反对子女报考大学,明眼人的父母会从“视力障碍”联想到“没法开车送孩子上下学”,从而阻挠自己的子女与视障人结婚……
视力障碍的“蝴蝶效应”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融入社会制造了虫虫障碍。面对视障人,人们的想象力总是十分丰富,其中的某些联想显然是源自不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