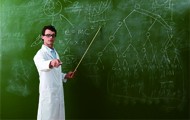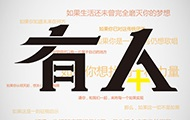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看见】没有这面镜子,世界该是公允的了
最近横空出世的女诗人余秀华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旋风,沉寂许久的诗歌界和评论界纷纷发声,其中多为肯定的言论,但也有部分持不同意见者。例如在评论家沈睿和诗人沈浩波的立场之间就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一个认为余秀华是难得的天才诗人,任何经过基本诗歌训练的人都能看出她写的是好诗;另一个却讲余秀华的诗写得并不好,没有太多可观之处。
然而,两人尽管在诗歌评论上的意见截然相反,彼此都看不上对方,甚至可说是很讨厌对方,但他们却在某个问题上不谋而合,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都反对诗刊和其他媒体用“脑瘫诗人”的标签来对余秀华进行推荐,只是反对的理由和出发点略有不同。

易被标签的残障者
沈睿反对使用“脑瘫诗人”部分基于政治正确,她认为这样讲缺乏对残障者的基本尊重与理解,因为我们不会管某个impotent (性无能)的男诗人叫“阴茎不能勃起诗人”。在这一比喻中,可以看到脑瘫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污名化,类似于性无能是对男性的侮辱一样。在网上讨论也可看到这种倾向,因为有很多人在澄清脑瘫不等于弱智,更不等于脑残,余秀华只是言语和行动上有一些障碍,她思路清晰,没有任何智力上的问题。
既然脑瘫这词听起来负面,容易让人误解是对智力的攻击,那么改用什么比较好呢?为此我查了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出品的《残障报道媒体指南》,在建议避免使用的术语一栏里,有这样一条“被多发性硬化症、脑瘫困扰等”,与其对应的建议则是“脑瘫患者”。显然,当前没有更好的词语可以代替“脑瘫”。虽然有人讲“身体有挑战”(Physically Challenged)更为政治正确,但它指向不明,无法准确传递信息,用起来并不理想。
同时,《报道指南》也指出:“应该避免以残疾为基础对人进行分类,应该只针对一个人而不是他的残疾来进行报道”。具体到当下的这个案例,也就是不应该将重点放在余秀华的残障上,而要基于她的诗歌艺术,将她作为诗人来进行推介。类似地,我们谈论一个具体的人时,可以附带提到她的身体状况(people with disabilities),但要明了这只是她的一部分,且并不必然是最重要的部分。
少数族群中的特例
沈浩波反对使用“脑瘫诗人”则主要是批评媒体媚俗、公众恶俗,他这样表述自己的感受:“当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媒体)在诗人余秀华前面,非要刻意加上脑瘫这个形容词,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
作为营销来说,这种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就连沈睿也不得不承认,她也是看了这个标题才读诗的:“《诗刊》用‘脑瘫’也真博得了我的眼球,要不然我也不会看余秀华的诗歌”。可见该方式相当有效,可以在短期内吸引到看客的注意力。当然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互联网时代永远有新的亮点会被挖掘出来,如果没有内在的、不竭的生命力,短暂的流行难免会搁浅。
更糟糕的是,它永远只是把少数人推出去,让他们作为群体的代表,博得公众的普遍同情,刺激其付出代价(消费),从而让当事人多少收获些补偿,中介者也获得他们希图的利益。但对于这个群体本身,意义又何在呢?除了符号化的激励作用以外。其实,面临残障和性别弱势双重挑战的女作家,从以前的张海迪到前些年走红的安意如,都有过非常正面的报道,但这个别者的成功似乎没能给女性残障者带来普遍的利益提升。
镜子会消失吗?
在余秀华的诗歌中,她这样谈到那个让她极不自由的身体:“我的身体倾斜,如瘪了一只胎的汽车……我的嘴也倾斜,这总是让人不快…..”,点睛之笔在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没有这面镜子,世界该是公允的了”。要怎么理解这句话?我的看法是:如果可以不用照镜子,发现彼此间的差异,世界可能本来就是平等的。
有点类似于《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残障概念,它指出残障是观念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单指伤残本身,更涉及到社会偏见和歧视,以及环境中有意无意给伤残者造成的障碍。——所以,当你去照镜子时,你看见的并不是客观的你,而是已不由自主被主观评价过的你。不论你眼中是美还是丑,都基于某个既有的社会标准,它显然是观念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照镜子的隐喻同时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的方向: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体,但总可以尝试来改变镜子。镜子本身应该成为一个中性物体,不再带有评判的功能,而是给你提供便利的工具,让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他人,帮助你们建立更便捷的沟通途径。简而言之,只有让原来的镜子消失,重新创造新的镜子(认知工具),这个世界才能真正实现平等、非歧视。

小结:
余秀华事件是一面镜子,从中可看到社会环境对残障者的态度,这种现象不可能通过揄扬和奖赏个别有才能的残障者得到改善,因她们会被当成特例来对待。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对于残障者的认知,残障者尤其是在当下环境中易产生镜像情结的女性残障者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