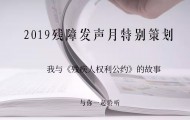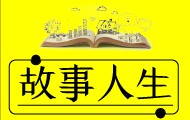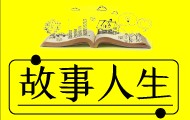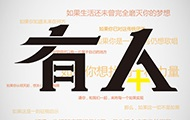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肢识】从跌跌撞撞到朦朦胧胧,我这摇摇摆摆的“残生”
我“生病”了,能“治好”吗?
从我记事起,父母带着我到处看病,公立医院,私人医务所,气功,按摩,针灸……只要听说哪里能治病的,都带我去了。但是大多都治不好。
记得有一次,妈妈在报纸上偶然地看到,北京的一家医院能“治好”我的“病”,就满怀期待地往医院寄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我的身体情况。
她对我说:等医院回信了,就马上带我去北京,把“病”治好。
听了这话,幼小的我欢呼起来,盼望着“病”好后,就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蹦蹦跳跳了。
然而,每天伸长了脖子盼呀盼,那封信却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音。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母把我送进了普通学校,在那里,身体上的不同让我成为了校园里的“少数派”,也受到了不少欺凌,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病”造成的,就算有一次,一位女生非常直白的告诉我:因为我走路姿势不好看,她们放学时,才不愿意和我结伴回家,当时的我也没有感觉有多难过。
因为那时,虽然受到了不少欺凌,但在班上,我也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俩的家离得很近,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谈论自己喜欢的男生;一起看彼此都喜欢的《少女杂志》;一起上学放学……班里的不少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俩之间的友谊,因为当时我们俩刚好一个是班里的女生中,身高最高的,一个是班里身高最矮的,班上的同学还常常调侃道:身高不能成为友谊的距离,我俩听到这话时,都可高兴了。
在整个求学阶段,我身边接触的几乎都是非残障人,尽管在校园生活中会受到一些欺凌,写字慢的特点也在中招考试时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觉得这是我性格软弱和没有足够的毅力多练习写字造成的,并没有太在意。
再说了,在校园里,我也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似乎和其他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上中专的时候,我终于得知我从小得的这个“病”俗称“脑瘫”,需要进行“康复”。我的内心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只是听说,我的这个“病”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残疾”是一种耻辱
大学毕业后,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校门,想着去找一份工作,努力挣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时,身体的状况,却让我屡屡“碰壁”。我大学学习的是会计,原本非常期待能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无奈,因为我的“残疾”,用人单位都不要我,要实现这样的愿望比“登天”还难。后来,被拒绝多了,我都不敢一个人去应聘了,每次招聘面试,都让我老妈陪着。
还好,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后,我终于还是找到了工作,先是在华润万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一家混凝厂。
在混凝厂工作的那段时期,我接触到了不少“残疾人”。这些“残疾人”大多目不识丁,也非常自卑,认为“残疾”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身有“残疾”理应被人“瞧不起”;似乎也无法明白“尊严”为何物……而在另一方面,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正常人”也不愿意接受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又脏又乱的寝室入住,有时,那些“正常人”见了身上有脏又臭的他们,都忙不迭地捂着鼻子“逃走”……虽然我的工作环境和住宿环境比起身边接触的其他残疾人来说,要干净很多,我却也免不了因为身体残疾而遭受到歧视。
“恐怕残疾人走到哪都会被歧视”我在心里悄悄对自己说道。
这样的情况,本来在求学时期对“残疾”没有什么概念的我,一下子自卑起来,我感到:“残疾”就是一种“耻辱”;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就我得了“脑瘫”这种“病”;我甚至想过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有“残疾”的人生就是不值得活的。
原来我也不是那么没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思念食品厂”的招聘公告,就去应聘,并且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老公,他很爱我,我们结合没有什么阻力,婚后的生活甜蜜而幸福。
2017年,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我当妈妈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了孩子降生的喜悦中,只是,我的父母在照顾宝宝的时候,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说:以前,我只需要照顾你一个人,现在我要照顾两个,你自己都不会带孩子。这时,我往往无力反驳,只能黯然神伤——我就是这么没用,谁让我是一个“残疾人”呢?
这时,我往往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儿子身上。
也还是那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个残疾人朋友微信群里,邂逅了一位社工。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参加她所在机构举办的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她就像我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关心着我,只要有合适的活动都会叫上我去参加。
2017年8月,在一次活动中,我第一次邂逅了来自河南省以外的残障朋友,其中,当我得知有一位导师是自己一个人从广州来到河南给我们做分享时,我简直惊呆了——我不敢相信,一个残疾女孩,竟然有勇气一个人坐飞机跑那么远。在我看来,她和我平时接触到的那些“残疾人”太不一样了,她的英语说得很棒,阳光、自信又很独立,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自己。
在和这位导师的聊天中,我得知有个针对残障女性开展的项目正面向全国招收学员,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了,后来,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得知我要一个人前往广州参加活动,面对旅程中可能会遇到的诸多未知的情况,全家人一开始的时候都表示了反对,后来,我最初在微信群里邂逅的那位社工,鼓励我——每个人都要学会长大,只有走出去才会遇见更多的精彩。
当我真正一个人踏上了去参加活动的旅途时,也发生了不少小插曲,比如列车上我无法自己去接水,在去活动的过程中不小心迷路了,手机又没装好导航软件等,但幸运的是这些小难题,我都通过向他人求助的方式顺利解决了。当我顺利到达活动地点,我忽然发现,独立出行的困难,也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从“残疾”到“残障”,我想和CRPD谈一场“恋爱”
在那次活动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以前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比如戏剧表演、瑜伽、拍电影等等。
也是在那次活动中,我第一次听一位导师讲起有关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其中导师讲残障的模式时分析的三个词——残废、残疾、残障,以及他所提到《残疾人权利公约》核心精神——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在培训中,这位导师的分享时间并不长,对于他所讲的那些有关《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我也没有理解得很透彻,但在他的讲解下,我隐隐意识到:
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一个特点,残障人士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我们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广州参加活动的那次,给我留下了此生都难忘的经历,从此我更盼望以后能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了。
2018年的时候,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我。我得到了去北京参加一个身体诗歌工作坊的机会。在那次工作坊中,我又尝试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为自己的身体写诗,第一次在乐队的伴奏下唱歌。这些尝试,让我感到自己与外面的新奇世界越来越“接轨”了。
也就是在那次工作坊中,我再次听在2017年那次活动中相遇的导师讲起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当这些知识和谈论我们的身体结合起来,让我对自身的残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能接纳自己,不再痛恨自己的残疾。
我很有幸两次在偶然中,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谋面”,只可惜每次见面都太匆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它,然而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它,因为在朦朦胧胧中觉得,在《残疾人权利公约》里,能找到我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
曾经,我在一个个优秀残障女性的帮助下走出了人生的“阴霾”,在未来我也希望能尽自己的努力更多地为残障群体发声。
《残疾人权利公约》我想与你谈一场“恋爱”,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相信如果有缘再遇到你,我眼中的“残疾”,也许能再次“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