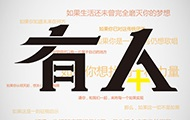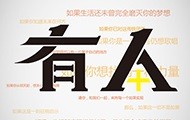【专栏】CSR需要私人定制

临近年尾,每个股民都在掂量“是持股过年,还是清仓观望?”,手中的股票“是业绩增长,还是下降了?”,那么年报行情,每一年多少都会有一波,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分配方案,往往都是一波或上或下的行情的推动力。但是,又有几个股民会看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呢?又有谁会关注一家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供应链管理、员工权益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教育机会提供、弱势群体扶持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呢?
偏巧,非政府组织NGO关注,因为要形成倒逼的趋势和独立第三方的地位,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以及可信性;更巧的是,我也关注,DPO关注,因为我想观察,DPO要监督,何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有残障用工数据等类似的指标出现。目前,在强制或自愿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很难发现企业雇佣残障人士的真实数据。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定义,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对自身责任理念与责任绩效的系统信息披露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实现,也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全面沟通的重要载体。
在CSR的10大原则中有一条:杜绝在用工与职业方面的差别歧视。具象到残障用工方面,就是禁止基于残障的用工歧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残障人平等就业或者就业反歧视。本文也将讨论点局限于此,不展开其他与残障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
在中国大陆,企业没有按照其职工总数的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就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指在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地区,凡安排残疾人达不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地方有关法规的规定,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资金。
这里不再赘述国内现有的法律规定,我们也暂且不谈就业保障金制度在当下的环境是否合理,如何修订的问题。至少目前就业保障金,税务局从企业直接征收,哪个企业都会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二;如果还不清楚,要么不差钱,要么想不到,要么不想管:于是,征收数额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出于全球CSR战略和要求,民营企业家出于企业家自身的道德素养,中小企业出于减税节省成本等等各种目的,愿意在残障人用工方面给予支持和事实雇佣。所谓事实雇佣,是相对于企业买残疾证,但不安排残障人去工作场所就业,仅仅为了免除税费的行为而言。
那么,企业的CSR在残障人用工上该如何履行呢?甚至说要不要履行呢?这是本文选取的设问。联想到最近,冯小刚导演的最新贺岁电影《私人定制》被广泛热议,电影《私人定制》的圆梦四人组为满足怀揣“奇葩梦”的客户,可谓来者不拒,个性化成全。而我们残障人就业,确实是个梦,是个中国梦,但绝不是奇葩和白日梦。或许企业在残障人用工方面的CSR履行倒可借鉴这部电影,CSR需要私人定制,下面我们就看看如何私人定制。

首先,为什么要私人定制。现阶段在企业的CSR战略和具体实施中,涉及残障人的内容多出现在对自闭症、智障、听障等儿童的关爱行动,即便有企业雇佣残障人,大多都非常低调,甚至不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怕宣传多了,自身又雇佣不了那么多残障人,出现道德审判和炒作之嫌,另一方面是企业大多在招聘流程、岗位设置等方面都是特别对待,也就是私人定制啦。这种私人定制受残障人因为相应职业生涯发展机会不平等而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的限制。目前,在残障人义务教育还没有达到融合,高等教育还采取单考单招,或者为残障人破格录取的阶段,为残障人的教育和就业采取私人定制的方式,确实实现和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残障人的梦想和需求。
但是,这并不是要私人定制的原因和结果。CSR需要私人定制,正是基于残障人无法实现平等就业机会的现状,要单独立法、制定政策,类似今年6月份日本刚刚通过的《差别解消法》和1996年香港的《残障歧视条例》。现行的就业保障金制度虽然本身就是法律保障的一种机制,但多以简单的罚款来理解和解决。为此,如果仅靠企业家的爱心和没有实质性约束的法律,或许可以解决个别残障人的就业问题,但一定不能具有普遍意义,不能改变整个残障社群的就业现状。

其次,谁来私人定制。是企业吗?No,而是党政机关、残联、中央和地方的国企,在谈企业CSR之前,如果我们的党政机关、中央和地方国企,不起带头表率的作用,反而首先要求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履行CSR,就是天方夜谭。难怪今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等7部门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意见》(残联发[2013]11号)的发出,就是要解决这个“首先’问题。意见中还规定“残联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残障人干部的比例”,这个更不要讨论,远的不看,就看中国妇联系统,妇女干部的比例高那是必须的,残联里少见各种类型的残障人,还要求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再次,私人定制什么。翻看目前残障领域的相关政策,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条款,例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相关规定中,一名盲人算2个指标。试问:为什么算2个?为什么不算3个、算1个、算1.5个呢?其实除了1名就是1名以外,无论算几个,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无行为能力,或者什么都不能干,智障人士更是如此。按照这个逻辑下去,当我们的残联工作人员与政府其他部门交涉“给残障人单独定额定岗定编制”时,政府部门的高明人士才会使用“反向歧视”一词,过度地给某个群体以优惠措施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即反向歧视。
是的,在理解平等和歧视的关系时,平等是同样的人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对相同的人以不合理的区别对待即构成歧视,但他们忘了还有一条,对不同的人以相同的对待也构成歧视。在残障领域是“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口号,在妇女领域就是“男女平等”,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一种误解。
多年来,残障人要么就被塑造成无能者,要么就被塑造成超人,残障人也乐见这样的形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对残障人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何乐而不为呢。而塑造身残志坚的形象使残障个人成为即得利益者,分明就是形象的扭曲。“身残志坚”只有在残障被扭曲的环境中才听起来别扭,因为这背后掩盖了很多违背残障人权利的事实和态度观念。否则,战胜个人的困难和局限的积极态度还是应当推崇的,就像其他非残障人积极地面对他们的困难和局限一样。长此以往,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走向过度保护的一面。
由此可见,观念改变是私人定制的前提。从医疗模式到社会模式,从慈善视角到人权保障,没有残障权利意识的启蒙,没有公民教育的深入,私人定制的内容只能是模仿的,效果只能是短暂的,最终都会被谎言揭穿。

最后,如何私人定制。观念改变了,有法律,有政策了,怎么做呢?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回答起来的确有挑战。残障社群的多样性和社会与残障社群的距离感、陌生度,有时候确实很难提出具体的措施,再加上笔者的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没有成熟的模式进行分享,如何私人定制,也只能停留在路径层面,以下提问,肯定不全,但也不用回答,仅供企业自审:
-企业是否定期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是否有披露残障人用工状况?
-企业内部什么级别的会议上,会涉及残障人用工状况的汇报?
-企业每年缴纳残保金的数额是多少?或者获得残联的岗位补贴及超比例奖励是多少?
-企业内部的部门设置中,是否有CSR部门?或者HR部门中是否设置相关岗位?
-企业是否知晓可以向残联申请企业内部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费用?
-企业有多少位员工的家庭中有残障人士?
作为以上自评,还要有一个名词要和企业人士分享:合理便利。这个词很容易和“无障碍”一词混淆,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请列位回头看:2013年第3季《有人》杂志中对话栏目《无障碍向左,合理便利向右》一文,会有清晰的解释。
行文至此,企业一定会问:我自己做好准备了,那么残障人在哪儿呢?别急,且听下回分解,2014年第一季《有人》杂志里面的《残障人去哪儿了》再见。
结尾之时,读者您一定会建议本文的题目应该更正为:残障人就业需要私人定制,而不是CSR,之所以用CSR,标题党是肯定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标题党,要把残障人就业问题上升到企业CSR的视野,应当成为考核企业CSR的履行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文明的国家,可以有懒汉上街乞讨,但绝不能有残障人无家可归,没有工作;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一定会充分保障弱势人群的权益,在其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手,给予爱心帮助;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残障员工一定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绝不刻意标识。
所以,本文的题目就这样也无妨,刚好符合电影《私人定制》圆梦四人组的口号:“成全别人,恶心自己”,也符合我的风格:“死磕自己,愉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