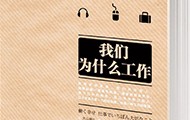【阅读】在颠覆中还原真实——盲人与《推拿》

在有着近两千万盲人的中国,竟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把目光投向这一群体,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毕飞宇老师的《推拿》填补了这一空白,且出手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正好,我打算从一个盲人读者的角度说说《推拿》的特色。我本人与书中各个主人公都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看见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如同看到我自己的往昔。因为与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共鸣,要想客观的、公平的评价这部著作似乎不大容易,所以以下我的所有看法都会带着个人感情色彩。
正好,我打算从一个盲人读者的角度说说《推拿》的特色。我本人与书中各个主人公都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看见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如同看到我自己的往昔。因为与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共鸣,要想客观的、公平的评价这部著作似乎不大容易,所以以下我的所有看法都会带着个人感情色彩。
《推拿》故事情节主要围绕按摩店展开,全书除引言和尾声外共21个章节,每一章节以一个核心角色展开叙事。按摩店仿佛是一个舞台,主角交替出现在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欢离合,这种叙事手法很容易把真实的生活戏剧化,但作者有着长期与盲人相处的经历,构成这些“戏剧”的材料有着坚实的依据,并未使读者产生情节夸张,脱离现实之感。
讨论叙事结构,文体特征不是我能胜任的,我的看法准备从故事情节进入。在初读《推拿》时,幸而我已经对作者有所耳闻,不然我就要把作者视为天人了,何以他的目光会如此毒辣,好像时刻在注视着我以及我的朋友们。有文章记述,鲁迅的《阿Q正传》在连载时就有读者到处打听小说作者“巴人”是谁,当他确知他不认识作者后,大松一口气,《阿Q》不是写他。在我初读《推拿》时,就有相似感受,如果说鲁迅用一个脸谱化的阿Q为一部分中国人画出了像,那么《推拿》则是给我们这个群体画出了一幅像。让我不假思索的举例来说明这种真实性。我会首先想到“小马嫖妓”,多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就有去洗头房买春的经历。其次就要提到十七章中沙复明和张宗琪下铺的两位同事留下女朋友过夜的情节,我本人就在上铺这个摇篮中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一件事。我不厌其烦的提到两段跟性有关的情节,除了这种情节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外,主要是我想籍此提出我的一个看法与我的盲人朋友们商榷。在对《推拿》的评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推拿》中的性描写是对盲人的妖魔化。我认为并非如此,首先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其次我们盲人也要正视自身的性需求。作者笔下并没有过分的对性爱场面展开渲染。只是把盲人还原成人去写,正视了每个人合理的需求。
以往涉及到残障人的文艺作品中,只给人留下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印象。把一个个残障人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勇士,着重强调残障人与命运搏斗的悲壮感,这在我看来,其实才是一种妖魔化。与这种无限拔高残障人形象的方式相比,《推拿》中对盲人全方位的描写才是对盲人的尊重。
如果只是以上这些对现实的简单重现,那么《推拿》也就不值得称道了。最重要、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做到了对盲人内心的深入了解。这种了解有悖于传统的看法,但给了盲人足够的客观与尊重,也给了盲人足够的剖析与真实。
在第四章描写都红演出后的一段文字最能说明问题。都红的自尊也就是盲人的自尊,而主持人的煽情就是社会对盲人的普遍认识。都红还沉浸在演砸后的内疚与自责中,主持人就已经开始热情的赞美都红的演奏。都红的自责表明了都红没有在演奏上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而主持人的夸奖则恰恰反映了社会对盲人无意识的轻视。原文中有一句话很富冲击力:
“都红想哭的心思没有了,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是苍凉。都红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能把盲人的自尊心挖掘到这样的深度,殊为不易,强调盲人自尊的同时揭示了社会的偏见。像这样深刻的、独特的视角还可再举一例——都红的美,在大导演为都红的美而赞叹时,整个推拿中心都震惊了。似乎他们平时都不知道都红的美,需要借助导演的目光来认识都红的美。当推拿中心的女推拿师向远方的朋友介绍都红的美时,他们只能用神经质的语言来表述一种夸张的语气。到底什么是美,对沙复明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他满脑子都在想着都红,却构不成一个关于都红的印象。这样的困扰纠缠着沙复明,以至于让他想去抚摸都红的脸,想在都红的脸上验证美。最终他抓住了都红的手,此时的沙复明似乎真切的感受到了美。然而这是真的美吗?这不过是让沙复明联想起少年时期的一次感动。这段描写揭示了一个被我们自身经常忽略的问题——盲人对美的概念不是直观的,而是存在于他人的评价和自我的构想之中。
以上我从情节的真实说到情感的真实,这两点都是从个案说开去。纵观整部小说,要找出一个贯穿全文的核心关键词,那么必是“命运”二字,小说中每个主人公仿佛都在一张命运编织的网中。在第六章金嫣和泰来这一节中,金嫣给泰来算了一卦。当金嫣用早已掌握的有关泰来的信息把泰来唬的一楞一楞时,作者写道:
“徐泰来傻在了那里,不知道他的命运里头究竟要发生什么。徐泰来自然是不会相信身边的这个女人的,但是,说到底盲人是迷信的,多多少少有点迷信,他们相信命。命都是看不见的,盲人也看不见,所以,盲人离命运的距离就格外地近。”
在我看来,作者这一看法格外切中要害,且不说盲人中还有一群人以算卦为生。就只说盲人平时常说的,“这辈子瞎了,可能前世是屠夫,造的杀业报应在了这一世。这虽然仅仅是一句笑谈,不可当真,也不会有人当真。但这其中也反应了盲人在无偿命运威压下一种宿命论的潜意识。
这种潜意识的来源,其实是一个排斥“盲人”这种非常态的所谓常态社会一直固有的观念,这种将之视为报应的命运论说,将盲人一点一点地打入卑微的尘埃里,只能供“常人”来同情。而最大的悲哀,是盲人们自己也或是为了逃避,或是自暴自弃,渐渐地竟在相信中,开始麻木、认命。
全文中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角色是王大夫。第十六章中,王大夫以自残的方式与命运恶斗,看似是王大夫以一个决绝的姿态与讨债公司对抗,实际上应该看成是王大夫在向命运咆哮。当警察再三追问王大夫是谁干的,王大夫的回答是我的血想哭。这样一句凝练的,像诗歌一样富有穿透力的语言道出了王大夫的痛苦,却道不尽王大夫的人生悲剧。小说开篇就交代了王大夫的弟弟是一个多余的人,是仰仗着王大夫的眼睛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里的“多余的人”应该看成是反语,恰恰指的是王大夫。现实生活中,像王大夫这样“多余”的人,并不少见。他们的意见,从来无人去关心,大抵,你一瞎子,啥也干不了,将来还有个人照料你,就挺好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自从有了弟弟之后,王大夫才感到了彻底的解脱。在第十六章王大夫喝退“好听的声音”后,有一段关于王大夫与父母关系的描写,这段文字就是对王大夫多余的人这一身份的注解。王大夫跟父母并不亲近,以至于在他这次疯狂的情绪宣泄之后才在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抓住父亲的手,此时的王大夫感到怪异,感到不适应。作者此处的描写真可谓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用冷静而不失温情的笔法展示了一幅血淋淋的现实场景。
小说在都红离开按摩店,沙复明紧急送院抢救后结束了,并没有告知沙复明手术后的确切情况。无疑,都红的离开和沙复明生死未卜这样的结局是灰色的、悲怆的。我的朋友中有人很不认可这样的结局,他们希望作者给出的结局是光明的、确定的。然而我以为只有悲剧式的结局才是与我们盲人沉重的生存现状相符合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只能让我们感到轻飘和无所依傍。悲剧所展示的才是生活的真实与无可奈何,悲剧对我们造成的撞击让我们沉默,让我们真是美好。
而,盲人的生活,抛开无法看到这一点,其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每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毕飞宇只是使用了盲人这一特点鲜明的群体在叙事,但如果单纯地只是因为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我觉得并不足以支撑《推拿》这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最关键的是,透过《推拿》这本书,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的无奈与悲哀、彷徨与挣扎。如果硬要说它是一种命运,那么,它其实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背负的。只是,我们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因此,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